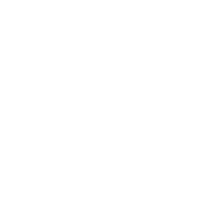五 十 載 輝 煌 路
五 十 載 輝 煌 路
張誠心
說起來也真巧,母校的50華誕,也正是我50周歲的生日。你說這是巧合,還是一種緣分?
回憶起1972年,我們當時在內蒙古藝術學校生活和學習的情景,感慨萬千。那時“文革”還未結束,破壞嚴重,校舍破爛,教學設備不全,經費短缺,可以說學校的各個方面都很落后。教室、琴房、宿舍都是磚砌的平房,有的已成危房,用磚垛頂著,10幾個人擠在一間宿舍里。但是,校園卻十分整潔,樹木蔥蘢,花草遍地,特別是到了春天,桃花、杏花、丁香花相繼開放,把校園裝點得幽雅、美麗,再加上錚錚琴聲,真真是一座圣潔的藝術殿堂。
軍事化的管理模式,使每個同學都自覺地養成了良好的生活習慣與嚴明的組織紀律性,早上必須6點起床出操,晚上10點一律按時熄燈睡覺,這一點是現在許多藝術院校做不到的。全校唯一的一個綜合性排練廳(是學校最高、也是最漂亮的建筑),充分發揮了它的綜合作用,兩個舞蹈班上課用,合奏課、合唱課用,開大會用,向領導匯報演出用,接待外賓用,元旦聯歡也要用,你說使用率高不高?
時勢造就英雄。也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,一批批有藝術天分的幼苗考進這所學校,經過幾年的學習和錘煉后,又一批批走出學校的大門,服務社會,為祖國的藝術事業添磚加瓦,貢獻力量。
1975年,我們這屆畢業生成功地排練演出了芭蕾舞劇《白毛女》,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,得到認可和肯定。從當時樂隊的演奏水平,舞蹈學生的技術能力和表演水平,以及舞臺布景、燈光、道具、效果的制作和裝置來看,可以說那是內蒙古藝術學校的全盛時期,創造了一個藝術高峰,即使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,也是一臺有水平的演出。
從1972年入校到今天,盡管已過了35個春秋,但當年藝校的往事讓我無法忘懷,許多老師的身影和音容笑貌常常在我的腦海里浮現。包玉山老師,吳葆娟老師,劉興漢老師,張大鯤老師,巴音滿達老師,他們都是我的恩師。在這里我衷心感激他們,并祝他們健康長壽,同時,也衷心地感謝曾經培養和關心過我們的每一位師長和學友。
2003年,我第一次回到母校,學校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,校容校貌煥然一新,沒有了昔日的簡陋模樣,感到非常欣喜。教學樓、舞蹈排練廳、琴房樓、辦公樓、音樂廳拔地而起,噴泉、雕塑、小花園里垂柳依依,花團錦簇,營造出幽雅的藝術氛圍。我為學生授課,并舉辦了圓號音樂會,目的就是要回報母校對自己的培育之恩,今后我將一如既往,繼續關心和支持母校的建設和發展。
最后,我想告誡在校學習的各位同學,現在學校的條件好了,但刻苦學習的精神不能丟!藝校的優良傳統與作風不能丟!